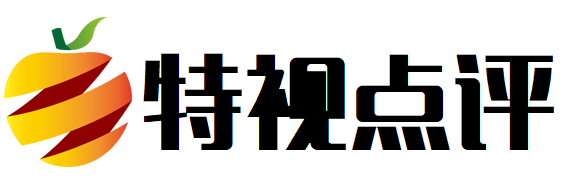关于国语的历史地位的最新点评答案内容如下:

《国语》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古籍,所记内容以春秋史事为主,不少记叙与《左传》相表里,《汉书·艺文志》将其与《左传》并列入“春秋家”,故自汉人以下,或径称之为“《春秋外传》”,而称《左传》为“《春秋内传》”。唐刘知几作《史通》,始别《左传》与《国语》为两种不同的体裁,而以《国语》作为“六家”,亦即诸种史学著述中的一家,即今所称“国别史”之首。清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于史部下无“国别”一项,而将其列入“杂史类”。无论何说,《国语》长期以来被视为一部基本的史学著作,是没有异义的。
不过,从严格意义上讲,《国语》实际并不是一部史,它的目的并不在于纪事;以国分类,亦不是它的主要特色。《国语》的特点在于它是一部“语”,“语”的本义是议论。《说文》云:“语,论也。”其解“言”字曰:“直言曰言,论难曰语。”是《国语》本为一部议论总集。古人从事教育的一个手段,即是收集前贤有关政治、礼仪、道德等方面的精辟议论,把它作为教材教给后人。《国语·楚语上》记楚大夫申叔时建议庄王太子学习的内容中,有一项就叫做“语”。叔时对楚太子傅说:“教之语,使明其德,而知先王之务,用明德于民也。”《国语》的名称,即是讲该书乃集合各国之语编辑而成。
《国语》作为先秦时期重要的史籍,其史料价值及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。以此,它受到历来学者的重视,并有多人为之作注,重要者有东汉时的郑众、贾逵,魏晋时的王肃、唐固、虞翻、韦昭、孔晁等。唐宋以来,各家之注多失传,惟韦昭《国语解》独存于世。北宋时,宋庠字公序,曾对《国语》及韦解加以整理,并作《国语补音》三卷,成为主要的传世之本。又有仁宗明道年间所刊之本,清黄丕烈重刊之,并作了校勘札记。于是自清代中期以后,明道本与公序本同为《国语》通行之本。
清代学者校注《国语》者甚多,大致可分为二类:一为全刊《国语》本文及韦解更加附注者,为补注性质;另一种则仅摘列《国语》及韦解有关文句加以校勘诠释,而以后者为多。最重要者为汪远孙之《国语校注本》三种,即《三君注辑存》四卷(“三君”谓贾逵、唐固、虞翻)、《国语发正》二十一卷、《国语考异》四卷。此外如刘台拱《国语校补》、汪中《国语校文》、陈瑑《国语翼解》等,又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、俞樾《群经平议》,也都有重要的校释成果。取补注性质者,较早有董增龄之《国语正义》,正文依公序本,韦注加“解”字,正义则加“疏”字以别之。清末民国间有吴曾祺的《国语韦解补正》,因其晚出,采摭各家之说较多。其后有沈镕撰《国语详注》,惟存《国语》正文,摘列重要词句,略加诠释,其性质为重注而非补注。徐元诰之《国语集解》行世最晚,而能网罗各家之说,取补注形式,较其前各书为详,从而更有利于读者对《国语》的阅读。
徐元诰的《国语集解》初版于一九三〇年,由中华书局印行。其在全刊《国语》本文、韦解全文的基础上,选择各家有关校勘及注释文字,参以己见,使历来国语研究成果备于一炉,颇便读者阅览。在校勘方面,为求《国语》原貌,其兼采公序与明道两个本子,择其是者而从之,而列其异文于《集解》之中。或据诸家之说,明其所采与不当采之理由。凡此,皆见《国语集解》在广泛利用各家校勘成果方面所做出的努力,经过这样校勘的《国语》正文及韦解文字,当较过去更为可靠。
同样,由于采纳了各家不少注释,《集解》也提供给了读者更多准确理解《国语》文字的方便。这些注释,有为韦解未采而为汪远孙《辑存》所收辑的贾逵、唐固、虞翻三君的注,但更多的是清人的各种注释。他们有的以文字音韵考释见长,有的以对某种文物制度的通晓见长,有的则以古地今释见长。《集解》援引诸说,或于某些缺注之处补注之,或对韦解某些错误的训释进行纠正,或对其尚嫌粗略的注释进一步解释之。
《国语集解》之疵误虽多,但能容纳清代以来各家校释《国语》之成果,两相权衡,仍是瑕不掩瑜。如能正其疵误,则可嘉惠读者,收事半功倍之效。爰加董理,标点全文之外,更着重校勘,共计写成校记一千一百余条,每条按序编号,而总附于每卷之末。原书所载旧序,则改为附录,刊于全书之后。全书由沈长云标点初稿并校出有关问题,而由王树民最后定稿,写成校记。时间既迫,又杂事纷纭,未能从容校勘,罅漏必然多有,幸祈读者不吝教正为感!
版权声明:本文来源于互联网,不代表本站立场与观点,特视点评网无任何盈利行为和商业用途,如有错误或侵犯利益请联系我们。